63岁惠英红不婚不育,穿着婚纱,苦等初恋50年
这半生风雪纷飞。
她在风雪之中,抱以春风十里。在战战兢兢的世界里,固执地爱一个人。
1浮世如流。
人事湍急而下。
什么都是急急急。行路急,爱人急。三天无音讯,立刻止损,换了天地。
没有人会等在原地,苦守一场幻觉。
除了惠英红。
63岁这年,她穿着婚纱,染红妆。在镜头前笑着,半是沧桑,半是羞赧,呼唤13岁时爱上的不归人。
“如果你回来,就在一起吧。”

可是,回不来了。
50年里,他没有音讯,查无此人。像云烟一样,消失于她的生命。
她真的找过他。
去异国,寻访老兵,向所有人打听这个人。
在媒体上刊登启事。
终于无声无息。
她多次提到他,满怀柔情与怅然:
“如果有天他回来,一定要他再讲一次‘我爱你’。如果他求婚,我会毫不犹豫嫁给他。”

他是短暂星辰。
是她生命里最温柔的花开。
人走了,花落了,就在记忆里长盛。
2他们相识时,她13岁。是一个小乞儿。
已经乞讨10年。
3岁起,她就带着比她更小的妹妹,站在湾仔码头的水门汀上,抱着路人的腿,乞讨,卖口香糖。
她早早知世故。
但这种“知”,全是不得已的悲凉。一旦讨错了人,就遭遇劈头盖脸一阵毒打。
“哪来的小乞儿,滚开!”
而她的身后,无人为她托底。
父亲被骗光家产,人一下子老了。母亲不识字,也不太通理,动则将她吊在房梁上暴打。
关键是太穷了。
人渣骗走了钱,台风卷走了他们仅剩的一切。
他们无家可归,在一栋破楼的楼梯下面,找了个角落,安顿一家人。

没有食物,靠小饭馆扔出的残渣度日。
就在这样的日子里,她的哥哥、姐姐全被送人。
她至今记得那个场景——
她在铁槛栏中,伸出双手,试图去抓住姐姐与哥哥,哭喊着:“不要走,不要走......”
撕心裂肺。

流光溢彩的天上人间,是别人的。
属于她的,只有充满一个困窘的、动荡的、无枝可依的童年。
就在这样的童年里,她饮恨咽苦,食遍辛酸,慢慢长大。
直到遇见他。
他是一个美国水兵。
很年轻,应该也不超过20 。是个混血儿。生得俊美。

也不知从哪天起,他一次次来买口香糖。买完了,站在不远处,看着她。
就是这样。
两厢讷讷无言。
她要卖口香糖,主动和他说话。一来二往,熟了起来。
逐渐聊了很多。
七天里,他谈了来处,说了恐惧,也知晓了她的身世,她的疼痛与悲欢。
他去不远的酒吧,买了薯条,送给她。
一包薯条,之于你我,是闲食。但从未被厚待的少女,却视为珍馐,珍爱万分。
他们坐在港口的栏杆上,晃着腿,聊着可有可无的事。

仿佛战争永不会来,人间永无疾苦,现实如云似霭,温柔地托着他们。
但离别很快就来了。
第7天的时候,他来找她。满脸戚戚色。
“我要走了,去越南,可能回不来了。”
万般不舍,也无济于事。
他将身上所有钱,都掏了出来,全部给了她。像是安顿至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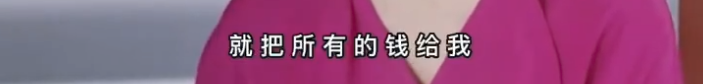
临行时,他问了她一句话:“Can you teach me hou to speak Cantonese I love you ?”

她说:“我爱你。”
他看着她的眼睛,以她的话,表他的意:
“我爱你。”
此后一去不返。
那时候,惠英红从早到晚等在港口,看到远归的游轮,渐行渐近,逐渐停泊。
看着每个下船的人,期盼他能从中走出,笑着走向她。
但次次落空。
她继续在贫困与卑贱中挣扎。
继续在日子的煎熬与世态炎凉中沉浮。

这是他所不知道的。
在他离开的岁月里,她有了转机。
但依然艰辛。
最开始时,她因为生得美,舞跳得好,被张彻导演看中,出演穆念慈一角。

此后她签约邵氏,凭借快、准、狠,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她敢从16楼跳下。

能忍着被壮汉狂殴几个小时。


从影岁月里,长袖善舞,百折不挠,创造过许多狠角色。
似乎什么都不怕,什么都狠得下心。
可到底不是铜皮铁骨。
许多次,她从高空坠下,或被男人群殴,无力反抗,一身伤痕。

她看着自己或肿胀、或悬吊、或骨折的四肢,疼得魂飞魄散。
但下一秒,她又重新站在片场。
严重的时候,无法行走,坐在武指的肩上,上半身继续打。腿像折断的树枝一样晃荡。
镜头仍忤着她拍。
多年以后,她想到那种剧痛,仍然心惊。
毕竟是女儿身,不是机器人,没有三头六臂,更没有即伤即愈的超能力。
但她别无选择。
她的身后,有一个贫困的家庭,像一个大胃,张开黑洞洞的豁口,需要她拼命去喂。
她必须马不停蹄。
必须竭尽全力之后,还要尽一分力。
穷人的孩子,没有资格软弱。
只有以柔软之躯,一次次地,咬紧牙关,去承担生命无法承受之痛。

终于,她尝透人间艰辛,将一生,活成别人的两生,甚至三生、四生。
在这跌宕的一生里,苦难如风,不留情地掠过她,千军万马地过去了,丝丝缕缕地过去了。
她被无端地剥了一层又一层,只剩下一个芯子。
可那芯子,一直是亮的。
4她会想到他。
想到那段温暖的往昔,那点纯粹的爱意,觉得生活或许还不算残酷,还值得等一等,拼一拼。
慢慢地,他成为微弱但不熄的灯火,温柔地照耀她。
扛不下去时,那点柔光亮起来,劝告她的孱弱,安慰她的委屈。
成为她生命的芯。
她继续往前走。
但前方,依然凶险无比,家破人亡。
1981年,父亲走了。
走时极尽折磨。
他瘦得不行,抢救时,浑身骨骼都在嚓嚓作响,似乎一根接一根碎裂。
她最终忍痛说:“不救了。”
她曾经想,如果父亲看见今天的她,一定会高竖拇指,说:“太棒了!”
但没等到这句话。
只能抱着他的牌位,对着电视机,轻轻说:“来看看我的第一部电影吧。”
后来又经历了母亲的阿尔兹海默症。

命途多舛的母亲渐渐忘记自己是谁。
忘记当年被卖到惠家,成为一个可怜的童养媳,吃尽千般苦;
忘记丈夫再娶;
忘记年长30多岁的丈夫如何离开家乡,来到香港,被骗得身无分文;
忘记年幼的儿女被抱走;
忘记了恨......
这是一种无望的清空。
记忆一点一点消失,直到什么也想不起来,变得幼稚又顽固。
作为女儿,惠英红的痛楚可想而知。

她照顾着母亲,近距离感受她的挣扎。
在《幸运是我》中,她将一个痴呆症老人的无助与悲凉,深刻地诠释。
因为这是她母亲的人生。
这部电影,让惠英红再次拿到金像奖影后。

荣光的背后,全是苦难在打底。
金色奖项的路上,多少老、病、死、离,正在发生。
不幸还在造访这个家。
2012年10月4日,哥哥惠天赐忽然死去。他也是演员,也拍打戏。
后来受重伤。
有一度为了塑身减肥,疯狂运动,不吃饭,忽然暴毙。被发现时,已经离去9天。
父亲走了。
哥哥死了。
母亲病了。
妹妹老了。
劫难轮到她自己了。
那时候,香港电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打戏不再时兴,偶像电影时髦起来。
她由炙手可热,变得无人问津。
困境就这样到来。
来得很快,几乎是一瞬间的事,再没有人找她。
她觉得自己没用,“很垃圾”,不吃不喝,也不见人,将自己关起来,吞下一瓶安眠药。

好在妹妹及时发现,将她救了回来。
醒来以后,她看着妹妹哭肿的脸,愧疚不已。
既然往前一步是困境。
退后一步是僵局。
那就继续往前冲。
她重头再来。
这一次,她不再用拳脚去表演,她用生命去演绎。
她完全成为角色本身——不是百分之几成为,是100%。没有旁骛的。

在拍《血观音》时,导演和摄影被她吓到,因为表演太有冲击力了。
有一场戏,是她一个人念经,用眼神诠释失女之苦。
镜头里,人彻底变了,再不是熟悉的红姐,而是一个心机深重又压抑痛苦的老女人。
剧组的工作人员毛骨悚然,说:“这是妖怪级演出吗?”
她再次赢得尊重与敬意。
《演员的诞生》里,她一出场,章子怡立即起立、鼓掌。称她是神。
合作过的导演则说,厉害到可怕。
千戏千面。
千面千人。
她创造了传奇。
可传奇之外,她依然是孤独的。
5她没有结婚。
63岁,无子无女。
始终在等。
等一个人回来,等良人出现。
有一年,她去美国领奖。领奖后,她举行了一个慈善晚会。到场的有一些美国老兵。
她问大家:“可有人去过香港?”
没有人。
“可有人记得,曾有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,在港口卖口香糖?”
依然没有人。
之后又千方百计寻人,依然一次次幻灭。她背过身去,抹去半生的泪水。

50年过去了。
这50年里,她的人生已如锦袍,可惜内有空洞,外有虱子。
属于外人的是风光,属于自己的是遗憾。
她想过无数次重逢:“如果有重逢,希望是擦肩而过,走过之后,蓦然回首,发现正是那个人。”

情不重不生婆娑。
爱不深不见菩提。
于是,我由不得不想,或许这场等待之于他,早已超越男欢女爱。
它成为信念。
甚至信仰。
有了它,“心有一座城,空等不归人”的艰辛,
带给她的,
不仅仅只有荒凉,
也有“众里寻你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已在灯火阑珊处”的生命体认。
在生命的“灯火阑珊”中,她站立着。
不苟且,拒绝随波逐流,放弃沾花惹絮的欢场作乐,无视银钏金钗的物欲,痛击泥沙俱下的席卷。
艰难地活成她自己。
那么,所有的等,成为生命的自省。成为人格的清明。
其实。
命运本如行歌,其中委曲与酣畅,回头看看,都是有限的。
一切得失与计较,信望与离丧,终究,都会被弹吹干净。只有你如何穿越迷雾,如何爱人,会最终留下来。
告诉世人“你是谁”。
告诉时间你来过。
惠英红电影
相关资讯
评论
- 评论加载中...